- 相关推荐
散文阅读环境描写
胡同已经消失,盖起了楼群,当年照在胡同口的那缕阳光依旧,照着现在的孩子们,照着记忆中幼小的我。有关散文阅读环境描写,请参考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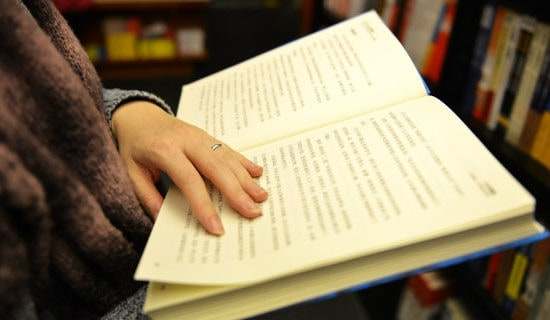
记忆里的胡同【1】
我搜寻记忆尽头,只得几幅景象片段。
我坐在床上,嘴里含着一个塑料喇叭,两个孩子站在床前逗我,我笑了,身体前倾倒下,塑料喇叭在床单上压碎了。
我在玩沙子,双手把沙子拢成长长的一行,然后我哭着在胡同里跑,两边的墙壁迅速后退,后来听母亲说,那是我在胡同口玩沙子,父亲哄我回家,我只顾着玩儿,他在我屁股上打了一巴掌,我哭跑着,屁股蛋子上的手掌印痕清晰可见。
母亲从菜市场抱着我回家,她给我买了一块儿西瓜,我咬了一口就趴在她的肩膀上睡着,醒来时已到胡同口,手里还拿着那块儿西瓜,瓜瓤上被咬过一口的地方有几根筋露出来,母亲的脖子上流着汗珠。
还有,父亲和母亲打架,我坐在床上哭,他俩面对面站着,他们的话我听不懂,耳朵里充满破碎的声音、愤怒的声音。
我的目光从他俩身上移到墙边的地上,那里有个矮矮的水泥平台,我想起平台上原本放着一台缝纫机,现在已经没了。
是的,我还能回忆起当时的心情,具体打碎了什么东西已不记得,却记得我很痛惜,家里的东西刚刚有了它应该呆的固定位置,让我觉得稳定、安全,却骤然被破坏,哭泣的我的心里不仅害怕,还有难过,沉默的水泥平台依然完好无损,看着它,我感到一点安慰。
还有呢,我那时候缺钙,刚睡着就“哇”地哭醒,父亲整夜蹲在床边吸烟,我一哭,他扔掉烟头抱起我,哄我再睡,但这是听母亲说的,不是我的记忆内容。
以前我家住在豫北纱厂生活区30号楼和猪圈中间的胡同里,现在30号楼还有,但胡同和猪圈已经没了。
我在一位朋友的博客里看到,她曾经住过的一条街现已改名,现在的已是一条与她无关的街,她只曾住在记忆中的那条街上。
周国平也在散文里写过,有一次回上海,小时候住过的街道由于城市改建已荡然无存,他说,又有一个自己在世界上存在的证据消失了。
由此,我联想起我住过的那条也已消失的胡同。
人心虽然孤独,但又相距不远。
把已在地球上消失的但是保存在记忆中的事物写下来,这是一种什么行为?这是出于对生命的爱的寻找。
凡是这样做的人都有丰富的内心,用心体会生活细节,喜养花草动物,细腻地观察生命每一种姿态。
他们对人生有来自精神层面的关照,所以需要用认知把曾经的自我从物质迁移中区别出来。
他们认为每一个生命都不应消失,既然无情的时空序列里已没有它的位置,就让它活在精神中。
这是对生命本身的爱,以承认生命价值为前提。
这种爱经常成为文学家们叙事的情感动机,因为有这种爱,木心才会在《上海赋》中记录老上海人的生活细节,本雅明才会在《驼背小人》中画下柏林的街景,普鲁斯特才会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描写山楂花,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会在《死屋手记》中讲述那群苦役犯,荷马才会在史诗中保存英雄们的身影。
对生命的爱体现于文学叙事,就扩展为对人类的爱。
别管叙自己之事还是叙他人之事,在文学语境里,无论是否自觉,都把被叙之人当作人类一员,从而具有自我面对人类的心理站位,所叙的事是自己知道的人类成员曾发生在世界上的事,对自己的关爱升华为对人类的关爱。
史铁生有一次出访欧洲,在一个环境优美的小镇里,听到远远地传来教堂钟声。
他立刻对这里有了故乡的感觉,他意识到,真正的故乡乃是一种无比辽阔、无比深情的心境。
故乡在哪里?在心里。
通过叙事寻找到的胡同、街道、田园都不再是现实空间里的那个,而是人类心理中符合故乡情感需求的那个,所以我听宗次郎《故乡原风景》能听出故乡韵味虽然我从未去过日本,所以我看朋友写的那条街能看出故乡的景象虽然我从未住在那条街上。
在文学中寻找的故乡是人类心灵的故乡。
我们带着对生命的爱,踏上记忆的路途寻找故乡,那是贮藏爱意的归宿。
我住在胡同里的具体年月呢?记不清了,绝对不超过四岁,在1980年之前。
年龄太小,记忆有限且不连贯。
记得每到某个季节很多人家都晒臭豆子,竹帘子上铺满黑色的豆子,在温暖的阳光下散发臭气,浓郁又亲切。
豆子很咸,就着馍吃很香。
我和一个小伙伴玩耍,渴了去他家喝水。
他喝水的方式很特别,桌子上放着一条吸饱了水的湿毛巾,他咬住毛巾吸水。
我看了觉得有意思,也咬那毛巾吸水。
现在想来不免感到恶心,但仍然有趣。
住户的房门钥匙都放在某个固定地方,门头上、墙缝里等等。
人回来了,从那个地方摸出钥匙打开门再放回原处,并不担心小偷。
有个青年男子每天搬一把躺椅放在胡同道路的正中间,坐下大模大样地看书,父母为他端水端饭。
他父母的恭敬态度令我们也觉得他很神圣。
有一次,一个乞丐进入胡同,他像胡同的主人一样,手拿书本对乞丐挥动,“出去吧、出去吧,这里是贫民窟,咱们都是一个档次的人”。
“贫民窟、档次”,这些词听来新鲜无比,成为我们竞相模仿的时髦词语。
那时候中国已恢复高考,不知他后来考上大学没有。
我们在胡同里扇“面包”,“面包”是用两张对折成长条状的纸叠成的正方形纸团,用力拍在地上,若把对方的“面包”扇翻过来就可将之赢入囊中,需要运用臂力和掌握角度,“面包”的质量更是决定因素。
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结实沉重、战无不胜的王牌“面包”,我们尊称为“老皮”,“老皮”都是脏兮兮的家伙,满身乌黑发亮的泥痂是它战功卓著的标志,在孩子们心目中地位无比尊崇。
胡同的南边是猪圈,猪舍与胡同南侧的民房只有一墙之隔,但我不记得猪粪臭味,只记得有很多大苍蝇,绿油油、明亮亮的苍蝇。
我曾抓住过一只,它的身子壳是硬的,在手里嗡嗡地震动,震得手心痒。
大人们急忙呵斥,“脏、快放掉”,我放了,看着它飞远,它的身子在阳光下闪耀着好看的颜色,奇怪它怎么会脏呢?
曾经,住在胡同里的我的父母是那么年轻,发黄的照片中,他们的容貌让我觉得像是陌生人。
他们在吵吵打打中一天天变老,我在他们的吵吵打打中一天天长大。
现在我看着老弱的他们,想着他们当年盛怒的样子,还有我的哭声、家里满地破碎东西,心里满盈慈悲的爱。
曾经,胡同离铁道很近。
深夜熟睡的我被火车鸣笛惊醒,朦胧中感觉到身边父母的体温和鼻息,身子缩一缩,再次滑入睡眠深处。
现在,我成家立业,住得离铁道远了,偶尔在半夜将醒未醒的时候,听到窗外传来悠远的类似火车鸣笛的声音,我顿然觉得回到了小时候,幼时睡在父母身边的感觉灌注全身,像普鲁斯特品尝到马德莱娜饼干和下午茶的混合味道。
清醒后,看看身边熟睡的妻子女儿,女儿的脸蛋儿犹如红苹果。
我想,终有一天,父母会离我而去,也终有一天,我和妻子会离开女儿。
将来长大成人的女儿会不会也在某个夜晚醒来,想起小时候睡在爸爸妈妈身边,看着她的孩子呢?想着,心很柔软。
胡同已经消失,盖起了楼群,当年照在胡同口的那缕阳光依旧,照着现在的孩子们,照着记忆中幼小的我。
三色青春三重门【2】
《骄傲岁月》是一部新写实主义作品,长于叙事,精于写人,以人记事,以事塑人,对现实生活有着全方位的折射,对青年情感有着深入的解剖,跨越军队和地方的空间维度,让人自然融入跳跃张弛的阅读快感当中,在陷入故事情节、沉静追随主人公足迹的时间天桥上,不禁随风畅想起自己的青春印记。
该书歌继过往、映接当前、细碎有序、繁复如链,通篇洋溢着健康、积极、向上的青春气息,兼具调侃、柔情、铁血三重亮色,确为一部正统实力派长篇小说。
到最后,能够骄傲地回想自己的青春,这是青春初始的梦雏,小说主人公周大田如蛹成蝶般的艰难进化,给“骄傲岁月”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青春文学不是颓废文学的代名词,赏阅《骄傲岁月》更能够让我们找到一股“气”,这股“气”可以用来充益当代青春文学,也可以用来充益当代青年的人生观。
一、调侃笔调下,青春贫穷只是一个笑话。
青春是充满色彩的年代,是成长成熟的年代,缘何当下许多青年,终于“惶恐不安”,在理想的的征程上颠沛流离,茫茫然而不知所求,只怪青春贫穷,让美好时光消失殆尽。
作者巧用调侃笔调,通过记录主人公的青春奋斗史,让青年一代的种种借口灰飞烟灭;也许在读这篇小说中你就会发现其中某个场景正是自己理想中的一个片段,某个角色正是自己在小说上的再现,品读文字感受活生生的人物跃然纸上,构筑起一个立体网络,让人读着不会觉得“陌生”,反而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作者将人物、情节、环境与现实生活巧妙的揉合在一起,用平实的文字勾勒出一幅平淡而又充满精采的“生活影像”,让读者更易深入小说,步入小说的精神境地,让每个来到这块“大田”的人都能有所收获,而不是两手空空,大脑芯片依旧没有储存内容。
二、爱情错乱飞张,确在偶然间追求,尽在柔情里回味。
“我常常渴望用自己的力量托举一片火红的枫叶,一片真正属于秋天的美丽的叶子,让她在我的掌心摇曳旋转微笑,我愿意把荷兰的风车吹得“咕噜咕噜”地转,逗她开心;我愿意把她带进挪威的森林,让她在阳光下的雪地上印下自己妩媚的身型……在这个世界上,美丽的情感多得不计其数。
大学校园,与燕子在旅馆那晚理论上的“1夜情”,带来更多的是对燕子的感激之情;费尽心思追求任静,最后只是在大脑的“内存”里占据了若干存储空间;步入军校,汗撒跑道只为一睹漂亮的女军医孔芳,然而只换来陌生的电话号码;开往成都的K388,与小文的偶然邂逅,却因志同道合,为追求的那份爱情画上了一个句号。
生活中,我们都在追求着属于自己的那份真爱,大田错乱飞张的爱情告诉我们:“1夜情”不是爱情,青春懵动的追求也不是真爱,孤独寂寞的寄托更没有结果,换来的只是“内存”盘上感情文件夹里的几个文档。
小说的字里行间没有华丽的词藻,但在人物刻画和感情描写上细致入微,让人感受到平实而又细腻,读起来如品一怀香茗,如饮一壶琼浆,回味无穷,沁入心脾,勾出思想的延展,不得不拍手叫好。
三、是否青春太小国家太大,铁血岁月找到灿烂意义。
“我把自己的体力、毅力、汗水献给了世界上最需要关照的人民,献给了善良人性的夺目光彩,献给了最大死神的逃遁战栗。
“我并不曾意料,粟子生命能有如此撼人心魄的魅力,如今明白,是因为我们在服务人民的大海里浮沉,有生尽力而为,逝去人民伤悲。
青春更需血性,而不是彻声大喊的奉献口号。
周大田用自己的体力、毅力和汗水浇灌着青春之花,让它在服务人民的伟大实践中灿烂芬芳,道出了青春男儿应有的钢铁血性。
《骄傲岁月》在抗震救灾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下让青春得以升华,让人们领略到人性的辉煌,给读者以心灵的震撼,让那些恍惚度日、迷失生活方向的青年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准自身价值的定位。
生活有千万种可能,让强者变得更强大,让弱者变得更软弱,或者让强者变得更软弱,让弱者变得更强大,所有结果都掌握在生存者自己手中。
人们擅长的是彷徨、迷茫和冲动,缺少的是智商的指针、精神的升华、认知的升级。






